說說我租住地下室的往事_站長休閑故事
推薦:訴說一個站長屌絲20多年的點點滴滴 小的時候是家長眼里的乖孩子老師眼中的好學生.一直被奉為數理化天才初一就自己學完了初中所有的數理化生的所有課程初三學完了高中的理科課程.初二的時候 開始參加各種競賽學完了模擬電路.每次考試理科的課程有一門不是滿分都會很有挫折感。
吃過晚飯了,可以詳細說說上午我發的那條廣播:有誰租住過北京的那種人防工程地下室?
一、
如果不是有些契機,很多人啊,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也就一輩子都在替別人為自己掘墓。
考慮到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人防工程“,先簡單說一下:人防工程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時期,“深挖洞,廣積糧”,一些大城市為了防止被轟炸,在市區里修建的一些地下室工程,這些地下室特別像地道戰的地道而不是今天寫字樓的停車場,有一個一個的許多房間,有公共衛生設備等等。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一些新修建的居民樓還是會修建人防工程,政府現在還有人防辦公室。
后來,北京的這些人防工程基本都被改建了,有些改成了廉價旅館,有些改成了居民活動中心,毫無疑問,肯定以前者為多。
2004年初,我大三的寒假。因為學校要求,我跑來北京某黨報實習1個月,托報社的一個姐姐幫我租房子,也不知道是那個時候租房市場不像今天這么發達,還是姐姐太忙沒有仔細找,她告訴我,因為我只住1個月,又要離報社近,只找到了一處地下室,條件很糟糕。我父母一聽,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讓我吃苦的機會,頗為高興的答應了。
那天,我跟著姐姐來到了紅廟一個居民樓門口。居民樓前的馬路對面是一個很大的工地,看不出要建的是什么建筑,但工地寬大的簡易圍墻上寫著”新光天地“,這四個字我是印象深刻的。
走過地下室長長的幽暗的通道,到了下面突然燈火通明起來,這里的床位一天只要8元錢,便宜的不可思議。我拖著行李到了房間,除了潮濕,并沒有發霉的味道。事實上,人防工程不同于一般的地下室,通風條件很好。

看到這個房間,有那么一霎那,我居然覺得很開心。
小時候讀童話,特別向往那些住在地下的小動物,土撥鼠,田鼠,鼴鼠,野兔……它們會在冬季漫天飛雪的嚴寒里,寧靜、舒適、溫暖的住在自己地下的小窩里。它們會建造許多房間,有的貯藏堅果,有的鋪上干燥的稻草,它們可以足不出戶躲過整整一個冬天,把皮毛保養的光滑柔順。
這樣的地下家園,會讓童年的我感到格外有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的想象很快就被衛生間粗大的水管下滴滴答答的滴水,地上和尿液混在一起的積水,以及那個看上去很不友好的室友所擊碎。
但我還是住下了,別無選擇。
二、
后來的日子,可以只講三件事。
就先從我這位室友講起吧。他比我大一歲,當時是蚌埠一所高中的美術生,已經在北京呆了好幾年,年年考美院,年年落榜,那時候他最愛和我說的一句話,就是”那誰誰畫的跟shi一樣“,但我從沒看見過他的作品。與他外表那種不良少年的面龐不同,他為人蠻實在,我們很快成了臥談時無話不談的朋友,他總是開玩笑的說”你們大學生都是垃圾“,我也會說,沒錯啊,都是垃圾。
那段時間我正在讀胡蘭成的《今生今世》,胡蘭成就是那年流行起來的。他看我看得津津有味,拿起來翻了翻,說,”這人干嘛的?“我說,”民國的一個作家,張愛玲的前夫。“見他貌似有興趣,我又說,”他經歷可豐富了,還跟著汪精衛干過,后來去了日本……“我話還沒說完,小伙子警惕的看了我一眼,說,”是個漢奸?“
我說,”是呀。“
他的手像過了電一樣,馬上把書扔到我床上,非常鄙夷的看著我說,”漢奸的書你也看,臟了我的手。“
我當時也很驚訝,我似乎理解了他說的”大學生都是垃圾“,包含了什么樣的意思。
用今天的觀點看,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小粉紅“,愛國愛得動物兇猛。其實,我當時就明白他為什么會這樣,并不是因為”地命海心“之類,他對國家、權力、社會等都沒有什么哲學思考。只是因為在這個城市里生活,他需要一個立場,需要一個歸屬。對于讀書思考都不多,社會經驗有限的他來說,國家,是手到拈來、既樸素又容易升華的最好歸屬。
我并不反對愛國,但愛國和愛生活一樣,是需要思考、審視才能判斷的,并不是什么發自內心的樸素感情。當然,很多人終其一生的自我歸屬,就是這樣的一個愛國者。
三、
在報社實習的日子很舒服,我每天在地下室睡到十點,因為地下室不開燈就是黑夜,所以睡眠質量很好。醒來后去報社吃午飯。工作上,領導對我很好,老記者對我也很好。因為是黨報,我的大多數工作就是去政府部門或是國企,拿到通稿和一些小禮物,如果是去網易搜狐這種地方,還能美美吃一頓,甚至觥籌交錯,回來把小禮物分一分,把稿子一發就好了。
我每天坐公交車去報社,有一天,和我在車站等車的正好是新光天地的建筑民工們。車來了,他們橫沖直撞,大呼小叫,推搡著我上了車。我的相機都差點被撞到公交車里的欄桿上,我感到非常惱怒又無奈,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是窗外工地上“新光天地”四個大字晃到了我的眼睛,我忽然想到,我,一個住地下室的本科生,和這些民工們有甚么本質區別?就因為學歷?還是因為我從事的是室內的文字工作?還是因為我躲在一個黨報里雖然我現在還只是實習生?……
想提醒一下大家,在2004年,HU先生“垂拱而治”的十年剛剛開始(這也是后發判斷了),第一屆(1999級)擴招的大學生才剛開始畢業,公務員考試常常報名還報不滿,社會上也沒有諸如“搬磚”、“IT民工”、“金融民工”這些自我嘲諷的詞匯和現象。那年頭,土著博士畢業進985還很容易,“白領”、“小資”這些身份還閃閃發光。那時候還沒有豆瓣,那時候《南方周末》如日中天,那時候我的人生偶像和職業偶像是《經濟觀察報》副刊一位名叫符郁的師姐,那時候……
扯遠了,扯回來。總之,早在那個時候,我意識到一個985大學的本科生,本質上和民工沒有區別,都是“勞工階級”,以后都要靠工資養活自己。這種意識在那時絕對不是矯情,而是一種焦躁與不安。
四、
我在報社跑的是經濟新聞,除了上面說的與政府國企打交道外,也干過一些別的好玩的事情。比如,曾經和西城區工商局一起端過一個賣竊聽器的小公司,我還扮作買主去踩點,謊稱老板娘要監聽有小三的老板。但現在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跑樓市那幾次。
2003年非典,北京房價停滯。2004年初,就有松動的跡象了。不過,那時候報社的老記者們都覺的北京房價漲到2008年奧運會就會到達峰值,奧運會結束就會跌。所以,我知道的買房子投資的人并不多。我要說的是有次跑樓市采訪,遇到一位老北京,人和氣的很,跟我瞎侃,有兩個體會:第一,現在四環的房價都六千了,聽說西城有的地方都快一萬了,這房價以后怎么辦啊?老百姓才掙幾個錢?肯定到頂了。第二,我們家原來就在城里頭,后來拆遷給拆到外頭來的,我們家祖輩就住里頭,怎么現在住在城外頭那老遠的地方了,當年也沒多少拆遷款。
他這第一個體會,我就寫在報道里了;這第二個體會我記在了腦子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就算是老北京,幾代的土著,也會有被拆到城外還沒多少拆遷款的境遇。事實上,在那短暫的一個月里,因為是正月期間,我曾跟著市民政局“慰問”過北京周邊多個郊縣,給五保戶發米面油,真正見識到了首都原來還有不少很貧困的地方,第一次聽見有些遠郊北京人講的方言,根本不是京腔,而更像是唐山話。
在很多立場、境遇、不可知的未來面前,地域——是北京人還是外地人,居住時間——是拿暫住證的還是剛落下戶口的,還是幾代的土著,本質上都沒有什么區別。

五、
實習期接近尾聲的時候,我爸突然打電話說來北京出差。其實,我在地下室住的日子并不覺得多么艱苦,相反,我覺得很充實,我那時候確實沒有什么社會經驗,所以一切都還算新鮮。唯一不方便的是地下室沒有信號,我每天要在外面的麥當勞里坐到十點多才回去。可是,一聽到我爸來了,我一秒鐘都沒耽誤,裝好行李就去賓館找他了。
道理很簡單啊,我雖然并不覺得地下室有多艱苦,但能住的舒服,我干嘛要住的不舒服呢?如果肉糜管夠,人人當然都要食肉糜了,“何況我哉?”(此處語氣請參考賈迎春)
那段實習經歷的一些感觸,在日后的十幾年的生活始終鮮活,我覺得,“階級意識”和“自我意識”是分不開的,沒有自我意識,就沒有自治的訴求;沒有階級意識,就沒有和誰自治、何以自治的行動。都說中國像一只雄雞,要我說,中國更像一只洋蔥,每一層就是一個階層。中間的那個芯兒,看不見,摸不著,但需要的時候就會剝掉最外面的一層,再有需要的時候就再剝掉最外面的一層。
廣東的北面都是北方,洋蔥芯兒的外面都是表層。
那些僅僅因為有個學歷的、有個戶口的,以及有點錢的、有一兩套房子的、在本地居住了好幾代的,甚至那些所謂“體制內”的,等等,在這個洋蔥里,如果你不屬于中間那個看不見摸不著的芯,那么,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層呢?能不能算出來什么時候就剝到你這一層呢?
根據我這些年的觀察,大多數人是不知道、算不出的。如果都知道,算得出,那,中國早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PS:大S老師說,我的樣本不全,作為《保衛大S老師近衛軍》的召集人,我擁護大S老師的判斷。所以,我也希望有同樣曾居住在地下室以及更差環境的朋友分享一下經歷。
作者:danyboy(來自豆瓣)
來源:盧松松博客,歡迎分享,(QQ/微信:13340454)
分享:細談那年初做自媒體經驗分享 記得那年我的自媒體成長之路,坎坎坷坷一路走來,在這期間也積累了許多經驗,借此機會分享給大家,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 相關鏈接:
- 教程說明:
站長休閑故事-說說我租住地下室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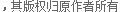 。
。